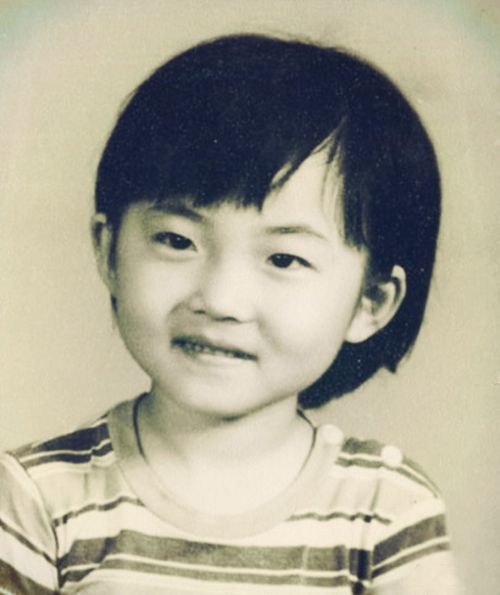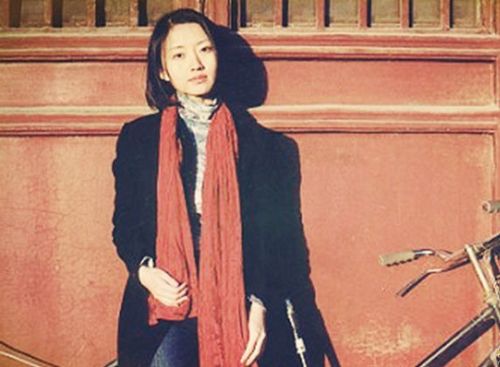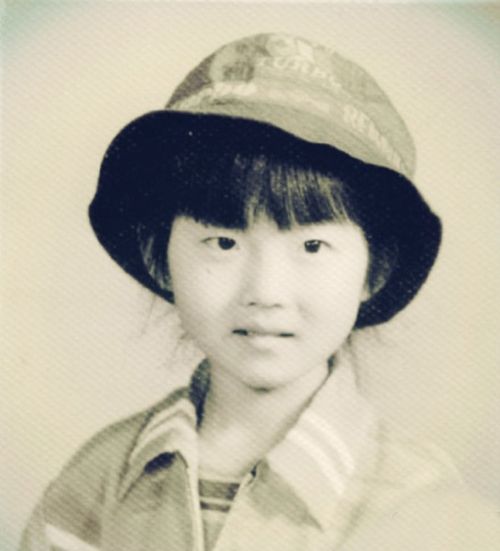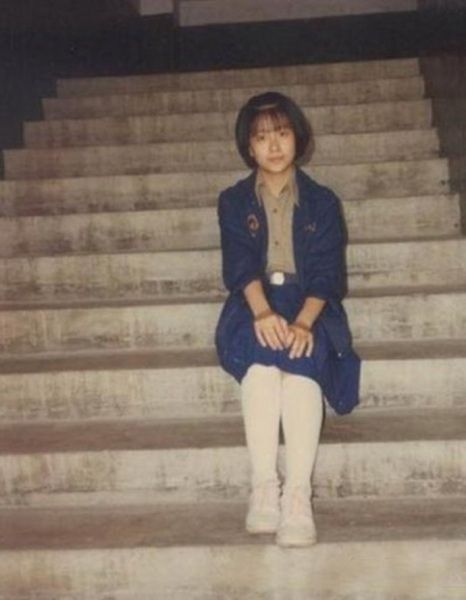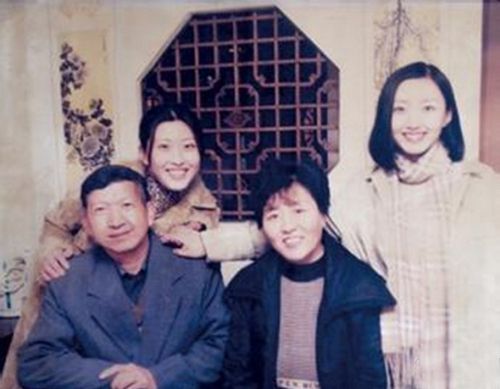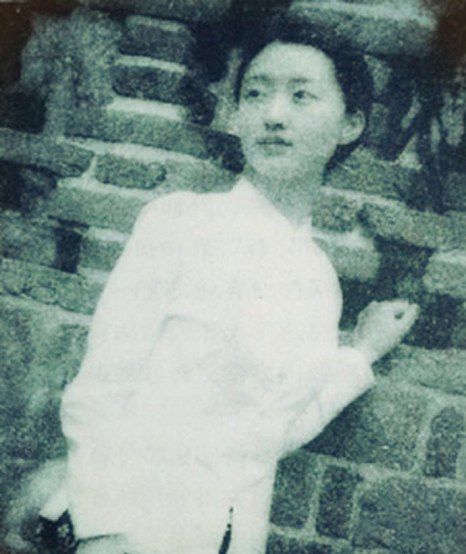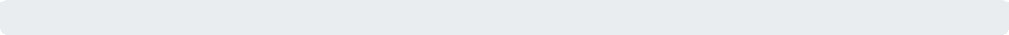柴靜童年可愛照曝光 書香門第背景揭秘(圖)
近日,有網友曝光了一組柴靜的童年青澀照,三好姑娘可愛的姿態一覽無余。
? ??1976年,柴靜出生于山西晉南的小城臨汾,住的是祖上傳下來的大宅子。父親從醫,母親執教,可算是書香門第。柴靜家在當地是一個很大的家族,曾祖父是個秀才,整個家族都住在從祖上傳下來的一座有300多年歷史的大宅子里。柴靜至今還記得童年時喧囂熱鬧的氣氛、雕花窗欞、木制油傘和那些古色古香的家具。
? ??柴靜的媽媽是個堅強獨立的女人。由于姥姥去世的很早,年幼的母親一直擔負起家中的大小事務,除了為姥爺和舅舅做飯洗衣服之外,還要刻苦讀書。那個時候,母親的成績一直都十分優異。在母親17歲時姥爺突發心臟病去世,當時,舅舅正遠在外地念書,為了不耽誤舅舅的學業,是母親一個人強忍悲痛處理了外公的后事。19歲那年,柴靜的母親當上了一名小學教師,此后不到10年,因為教學業績突出,她被評為山西省第一批特級教師,不久又被任命為臨汾某小學校長。在這期間,柴靜的媽媽結識了善良執著的父親。
? ??在柴靜的出生之后,柴靜的爸爸媽媽忙著工作,很少能抽出時間照顧小柴靜。但身為教師的母親并沒有因此怠慢對小柴靜的教育。但身為教師的母親并沒有因此怠慢對小柴靜的教育。在柴靜兩歲的時候,母親就開始教她識字。母親用紙板剪成四四方方的卡片,在正面寫上“日”、“月”、“水”等字,背上寫上這些字的漢語拼音。母親把做好的認字卡片用繩子穿起來,做成一串特別的項鏈,套在小柴靜的脖子上,讓小柴靜撥弄著卡片,提高學習認字的興趣。當別的孩子還在呀呀學語的時候,聰明的小柴靜在母親的培育下,已經認識了很多字。
? ?由于識字比較早,柴靜4歲就進入小學了,為了照顧小柴靜的生活和學習,母親把柴靜帶到自己任課的班級,讓她坐在最前排,和其他7、8歲的孩子一起接受教育。雖然母親也知道柴靜可能聽不太懂,但仍讓她堅持聽課,每天放學回家還背誦和默寫課文,即使柴靜對很多課文似懂非懂,她還是會興致勃勃的閱讀它們。再稍大一點,母親就開始為柴靜訂閱各種兒童報刊。并在家里騰出一間小屋子為她當作書房。每天放學回家后,小柴靜都會自己拿著小板凳坐在小書房里看小人書《岳飛傳》。柴靜對文字的敏感與生俱來,小小的年紀,對所有寫字的東西都十分感興趣,無論是父親訂閱的《中醫雜志》還是母親的函授書籍,她都能讀的津津有味。
? ??在柴靜上四年級的時候,媽媽調換工作,全家人都跟著她搬到她所執教的學校。小柴靜的行李只有兩件,一件是爸爸開完藥后留下的漂亮小藥盒,里面裝幾枚硬幣。還有一件是一本《唐詩三百首》。帶著這些東西,12歲的柴靜由小學升上了中學。13歲時,柴靜接觸到了廣播。她開始貪戀廣播里的熱鬧人聲和深入骨髓的歌。柴靜從那時才知道,廣播可以給人帶來一個如此新奇的世界,那一刻,柴靜夢想著能做一個電臺的廣播主持人,夢想著自己有一天能離開這個地方,過上一種另外的生活方式,自己要“更自由,要過和身邊的人一種截然不同的生活”。
? ??1991年,15歲的柴靜到湖南長沙讀大學,對廣播的喜愛依然不減,最喜歡聽音樂排行榜和談心節目。后來她終于鼓起勇氣,寫信給湖南經濟電臺紅極一時的主持人尚能表達自己做主播的想法,她說:“可否幫我成就夢想?”這句話促使了這位名主持馬上給柴靜打了電話,讓她去面試。七月份的長沙,天氣酷熱,柴靜借用學校廣播站錄節目,錄完以后,汗水把衣服全都浸透了。面試通過以后,柴靜開心極了,她開始做她的第一個節目——《另一種聲音》。
第一次坐到真正的演播室里,柴靜沒有恐懼和緊張,她覺得自己就屬于這個地方。此后,她每天都會帶一沓稿子和磁帶去做節目,整個暑假她沒有回家,留在了長沙做節目。那段日子,她和家里失去了聯系,常常翻箱倒柜地湊足5毛錢,跑到樓下買一袋最便宜的方便面,計劃著吃一整天。長沙很大很熱鬧,但是無親無故的她卻倍感孤獨,每天都在過著同樣的生活:騎著自行車去做節目,然后再騎車回來。即便如此,她仍然覺得很快樂、很安心。
? ??日子就這樣在忙碌中一天天過去,轉眼到了畢業的時間。柴靜在學校學的是財會專業,畢業后被分配到家鄉山西太原鐵路局工作。恰好長沙當時要成立一個新的文藝臺,柴靜去應聘,考核之后就留下了。她毅然辭掉在別人看來既穩定又舒適的工作,帶著戶口和工作關系到湖南文藝電臺做節目,開始了自己的職業生涯。在簡陋的租住房里,柴靜從來不會感覺苦悶,因為心中有夢,她堅信,這些困苦會在不遠的將來成為過眼云煙。
? ??柴靜白天忙工作,到了晚上,與她相伴的只有廣播中的聲音。她喜歡聽新加坡電臺林偉的《點一盞心燈》,他說:“與其詛咒黑暗,不如點燃燈火。”這句話讓柴靜感觸很深,她決定做電臺午夜節目。柴靜就和電臺的領導申請做一檔午夜節目,甚至可以不要工資。隨后,她創建了名為《夜色溫柔》的晚間節目,一做就是三年。
那時的柴靜只有19歲,年少的她心里只想著去實現心中的這個夢想,全然不顧自己身處異鄉的孤獨與寂寞。柴靜說:“一個人為自己的工作神魂顛倒是多么幸福。”那個時候她主要是接聽聽眾打來的熱線電話,什么事情都談。其實那個時候連她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去幫助別人排憂解難,畢竟她只有19歲,但是想用聲音激發一個有想象力的世界,想用聲音為更多的人趕走寂寞。她只需要說“我在,我聽到了,我懂”這樣的字眼,只要有一顆真誠的心就足夠了。
? ??經過一段時間之后,柴靜主持的這檔《夜色溫柔》變得十分紅火,之后的幾年,她基本都是在電臺度過的。柴靜在每個夜晚用真誠的聲音陪伴著孤獨的人們,她的聲音被越來越多的人們所熟知。在節目里,柴靜常常會接到從北京、香港、西藏等地慕名打來的電話,她去大學里做演講的時候,時常都會有桌椅擠壞的場面出現。
柴靜22歲的時候,順利地當上綜藝部副主任,成了湖南最著名的主持人之一。五月的長沙,茉莉花開,景色怡人。凌晨兩三點男人們成箱成箱地喝著啤酒,女人們吃著東西。柴靜經常能看到大街上享受著這種安逸生活的男人和女人們。她仿佛看到了自己未來的生活,有種莫名的恐懼讓她感到害怕。
柴靜對現有成績的不滿足,使她幾經考慮做了個令所有人驚訝的決定:辭職去北京讀書。她不甘心讓自己的生命就這樣達到頂峰,她需要尋找可以不斷超越的未來。她放棄了自己已經擁有的光環,到北京廣播學院做了一名學生,睡在藍白相間的格子床單上,學的是電視編輯,生活簡單而有激情。
? ??到北京廣播電視學院不到半年,一次偶然的機會,她在《三聯生活周刊》上看到一則招聘廣告。她打電話過去時對方說已經招聘完了。“你們不是想要優秀的記者嗎?這還有期限嗎?”她的一句話,給自己創造了一個機會,對方讓她第二天去試試。第二天她去應聘,負責招聘的人看看她說:“你長得挺漂亮的,不愁沒出路,回去吧。”就這樣,她被打發回來。沒過多久,《三聯生活周刊》給她打電話說他們要做一個封面周刊,問她做不做,柴靜二話沒說,立即答應下來。她用了三天的時間寫出兩萬多字的稿子,就在她放假準備回家時,編輯打電話說讓她把兩萬字改成兩千字,她用了兩個小時把稿子改完,跑到車站時離開車還有五分鐘。之后,柴靜在北廣[微博]的日子一直在做《三聯生活周刊》的兼職記者。
當柴靜在《三聯生活周刊》做得順風順水的時候,湖南衛視邀請她做談話節目《新青年》的主持人,當時《新青年》是湖南衛視改革后的一個新欄目。柴靜答應了,于是她開始一邊上學,一邊在電視臺做《新青年》的主持人。她在做節目的時候,采訪了各行各業的名人,如,米丘、黃永玉、蔡琴、張朝陽、方興東、吳士宏等。柴靜當時是初生牛犢不怕虎,為了證明《新青年》是文化先鋒,就做了一期關于20世紀 70年代新銳詩歌的話題,請來號稱用上半身寫作的女詩人和用下半身寫作的男詩人做嘉賓,事后證明她的這次挑戰成功了。柴靜在節目中變得越來越成熟,她總是能將生命中的偶然與必然的交匯、世事的滄桑浮沉刻畫得玲瓏有致。
? ??一個喜歡挑戰人生未知極限的人是不會安于現狀、按部就班地生活的。北廣畢業后,柴靜并不滿足《新青年》中駕輕就熟的工作,于是進入了中央電視臺“東方時空”的《時空連線》節目,做記者兼主持人。這對柴靜而言,是一個巨大的改變和挑戰。在央視工作之前,柴靜沒有受過什么挫折,但是來央視做節目之后,一下就蒙了,不能指望別人手把手地教你,只能自己不斷地摸索學習。
柴靜在沒有名校的學歷背景、不是新聞專業出身的情況下,度過了一段痛苦的適應期。文靜柔弱的柴靜開始時被同事認為不適合做新聞記者,當時她的壓力特別大。柴靜為了做好節目,從蹲馬步開始學起基本功,流汗流血、風吹日曬。她用最笨拙的辦法,像螞蟻一點一點地搬運食物一樣,一步一步竭盡全力地去學習,自己做策劃,觀摩同行的節目,上機編節目,每天都待在演播室里,熬夜到凌晨三四點。
那時候柴靜在采訪前,一定是要求自己花很長時間準備做足功課的。有時候,采訪完了夜里編片子編到三四點,然后送到臺里。柴靜是臨時工,進不了大門,只能請導播到大門口來接帶子。當時柴靜住 18樓,回去太晚電梯停了,好不容易爬上去,編導打來一個電話說有問題就再爬下來。
? ??柴靜能從一個文藝青年成長為獨立思考、探尋真相的新聞斗士,經歷了一個不斷學習的過程。剛進中央電視臺的第一年,柴靜完全找不到做新聞的感覺,不知道如何提問,真正開始找到做新聞的感覺是在采訪新疆地震時。
當時負責人白巖松對柴靜說:“去喀什,給你半個小時去收拾一下東西。”凌晨,到了喀什,落腳在一片瓦礫、斷壁殘垣之中。人們正在舉行葬禮,柴靜根本來不及去思考什么是新聞,新聞就像一盆水兜頭澆下來。倒塌校舍旁的兩個小女孩,從廢墟中走出來的老大爺,倒騰的半截房里濕漉漉的被子,讓柴靜活生生地感受到了什么是新聞,讓柴靜找到了做新聞忘我的感覺,找到了新聞中最鮮活的元素。
之后,柴靜進入《新聞調查》,她更喜歡到現場去發現,深入一線進行采訪。柴靜覺得自己在《新聞調查》中找到了自我發展的理想平臺。新聞記者不僅成了柴靜的職業身份,也成了柴靜的生活方式。

? ??2003年,柴靜參加了《北京“非典”狙擊戰》的拍攝,成為最早冒死深入非典第一線采訪的記者之一。驚心動魄的現場氣氛、搖晃的鏡頭、柴靜身穿白色防護服的瘦弱身影和蒼白的面容給觀眾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
熟悉柴靜的朋友著實為她捏了一把汗,節目播出的當天晚上,柴靜接到了數量前所未有的電話,感動之余,她沒有想到自己竟然認識這么多人。但是一整晚柴靜都沒接到媽媽的電話。這讓柴靜心里感覺不安。直到播出的第二天晚上,柴靜才主動打電話給媽媽。柴媽媽在電話那頭說:“我昨天在鄰居家看了節目了。”邊說她邊哭了——直到那個時候,她才知道柴靜最近的幾天里做了些什么。
但是柴媽媽并沒有指責柴靜,反倒幫她出起主意,她建議柴靜采訪在國際上享有聲望的流行病學權威何大一教授,還建議她做關于流行病傳染鏈的調查。后來,當柴靜要去艾滋病孤兒村采訪前,她給母親打了電話,母親在電話那頭猶豫了一會兒,最終還是說:“去吧,媽媽支持你。”
柴靜說,如果母親狹隘一點,給她一些阻撓,她可能在做類似這樣有危險的選題時,就不會太投入。現在,柴靜會就她面對的一切都跟母親溝通,比如何處理和領導、下屬的關系,如何應對工作中的突發事件。母親往往會以一個過來人身份,給她許多建議。
? ?? “非典”之后,柴靜離開演播室,從主持人成為了一名調查記者。她堅信:“除非親身抵達,親眼所見,親耳所聞,努力發掘,否則就不可能認識事實真相。”“做新聞要有笨拙的精神,不要不假思索,”她說要對評論有警惕,要對真相有潔癖。”
正是這種執著追尋真相、獨立思考的精神使柴靜對新聞調查有著獨特的見解:真正的調查報道就是探尋未知的過程,是不斷遇到障礙、克服障礙的過程。沒有未知就沒有調查。調查是以已知為起點的,不需要還原已知,而是探尋未知是什么。最精彩的地方往往就在你沒有設計到的細節中。
對柴靜來說做記者不僅是她的職業身份,也是自己生存的一種方式,因為調查真相就成為她的天職。柴靜著迷于這個真實的世界,愿意靜下心來沉浸其中,去領略那些撼動人心的地方,去體會黑暗深處的光明。
? ?? 隨著時間的推移,柴靜的主持風格日漸成熟,她不再是那個在最初會炫技的主持人——“你看,我的問題多漂亮,我把對方問倒了,我贏了。”柴靜深知這對于解決問題毫無幫助。現在的她經過不斷的思考,明白了自己節目的重心。不輕易做出褒貶,要做的是細節的探究和幕后真相的挖掘,能讓對方自由地表達,幫助公眾得到盡可能多的真相。
真正了解到世界復雜性的柴靜沒有輕易責難和贊美的習慣,更多的是學會了寬容和體諒。今天的柴靜是做新聞的楷模,這個昔日的文藝女青年成了一位名副其實的新聞斗士,永遠獨立地思考,永遠與真相站在一起。
? ??柴靜坦言,三十年來她努力從一個非常理想主義的大的共同體中把自己剝離出來,離鄉背井,就是為了找到自己。來京工作十多年的柴靜至今仍然租住在一個一居室的小屋中,但她表示自己對此從來不在意,“生命不是一張屬于你的床鋪,生命有時就在一瞬之間”。
當有人向柴靜提問:“柴靜,你幸福嗎?”聰明的柴靜沒有透露個人的感情生活,是用胡適的一句話來回答:“怕什么真理無窮,進一寸有一寸的歡喜”。即使開了一輛老掉牙的破車,只要在前行就好,偶爾吹點小風,這就是幸福。